我是芜湖人,刚从河南辉县回来,实在忍不住想说:对辉县5点印象
作者古巷之中漫步作品声明:个人观点、仅供参考
印象一、郭亮挂壁公路:凿在绝壁上的硬气,比想象中更撼人
看见郭亮挂壁公路的那一刻,才懂“人间奇迹”四个字的分量:整面百米高的绝壁上,35个天窗顺着山势蜿蜒,远看像串在红石头上的银环,近了才发现,每个天窗边缘都留着当年钢钎凿过的糙痕,深浅不一,有的地方还嵌着细碎的石屑,摸上去硌得手心发疼。跟着一位背竹篓的老汉往洞里走,刚进洞口就觉出凉来——岩壁上渗着水珠,顺着凿痕往下淌,滴在石阶上“嗒嗒”响。“五十年前,俺们十三个人,白天抡锤到胳膊肿,晚上就睡崖边的山洞,就想着凿出条路来,让娃们能走出山。”

老汉用旱烟杆敲了敲岩壁,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混着风穿过天窗的“呜呜”声,像极了当年凿山时的号子,在洞里绕着圈,钻进耳朵里,竟有些发烫。走到中段,一辆农用三轮车突突地开过来,车灯扫过洞顶,惊起几只蝙蝠扑棱棱地飞,翅膀擦过耳边时,带起一阵裹着岩屑的风。等车过去,往天窗外望,云海刚好漫过对面的山尖,黛色的山脊在云里露出来,像浮在奶白里的墨点,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,风卷着崖柏的香气往肺里钻。

印象二、百泉湖:三千年泉眼泡着的岁月,比镜湖更显古意
四月的百泉湖,比芜湖的镜湖多了份千年沉淀的静——湖边的连翘开得泼泼洒洒,金黄的花枝垂到水面,把泉水染成了蜜色,风一吹,花瓣落在水里,像撒了把碎金,跟着泉眼的泡泡慢慢漂,连水流声都显得格外轻。湖中心的涌金亭,红漆柱子褪得只剩斑驳的色块,木梁上的彩绘被岁月磨得模糊,只有几处还能看出青蓝的底色,却透着股老得从容的劲儿。

亭子里坐着位穿中山装的老汉,手里攥着根树枝,在地上划拉着苏东坡的诗句:“当年东坡在这儿饮酒,用泉水泡茶,说比江南的水还甜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,湖心确实有半截石碑斜插在水草里,“人民百泉”四个字被鱼虾啃得缺了笔画,碑身上还缠着几缕绿藻,却越看越有味道。绕着湖走,能看见泉眼在水底咕嘟咕嘟冒泡泡,像撒了把碎银,阳光照下去,泡泡泛着光,连水底的鹅卵石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有个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石阶上,手里转着个旧罗盘,说这湖底藏着千年的泉脉,水永远是温的。

印象三、八里沟:太行山里藏着的“江南”,比水乡多份野趣
往谷底走的石阶上,野葡萄藤爬满了岩壁,熟透的紫葡萄掉在地上,踩上去“咕叽”一声,汁水能染紫鞋底,甜香顺着鞋底往上飘。走到“一线天”时,前面堵着个穿汉服的姑娘,水绿色的裙裾卡在石头缝里,她回头笑,脸上的胭脂被汗水晕开,像朵沾了露水的芍药:“老乡,拽我一把呗?”我们俩连拉带扯地挤过去,冷不丁有只猕猴从头顶的岩壁上跳下来,抢走了她手里的油纸伞,蹦跳着往树林里跑,伞面的碎花在绿叶间晃,像只飞远的蝴蝶——这野趣,是芜湖的赭山公园、镜湖岸边都见不到的,鲜活得让人忍不住笑出声。

谷底的桃花湾,戴草帽的艄公撑着竹筏从远处来,鱼鹰立在船头,脖子上系着草绳,看见人就偏头叫两声,声音清亮。阳光透过竹筏的缝隙洒在水面上,波光粼粼的,恍惚间竟以为到了芜湖的青弋江,可再听风里裹着的太行松涛,又觉出不同——这里的水,是灵动里带着股山野的劲,软得让人想放慢脚步,又野得让人忍不住好奇往前探,每一步都有新的惊喜。

印象四、万仙山:云海漫过山尖时,比芜湖江雾更壮阔
清晨五点多,山风还带着凉,云海从山脚下漫上来,起初是淡淡的白,绕着黑松的枝丫缠成轻丝,像给树披了层纱,再往上走,雾越来越浓,把整片山林遮得只剩隐约的绿影,连脚下的石阶都变得模糊。等太阳慢慢爬上来,云海突然被染成了金红,漫过远处的王莽岭、昆山隧道,黛色的山尖在云海里露出来,像浮在奶白里的墨点,又像仙人的棋子,散落在棋盘上。风从耳边吹过,带着松针的清苦和泥土的湿润,伸手去碰,竟能接住松枝滴下的水珠,凉丝丝地渗进掌心,连心里的浮躁都被浇透了。旁边的当地人笑着说:“这是万仙在‘晒云’呢,每片云里都藏着山的灵气,不是天天都能看着的。”

往黑龙潭走的路上,石阶上覆着薄薄的苔藓,踩上去要轻轻放脚才不会滑。沿途的黑松林密得能挡住阳光,只漏下细碎的光斑在地上跳,像撒了把碎金。走到潭边时,云海刚好漫到潭面,潭水映着云,云裹着潭,分不清哪是云哪是水,恍惚间以为站在芜湖的长江边,可再看身边的红石崖,又觉出太行的独特——这云海,是把江南的柔,融进了北方山的刚里,既有云海的软,又有山石的硬,让人忍不住站在风里,多吸几口带着松香的空气,只想把这画面刻在心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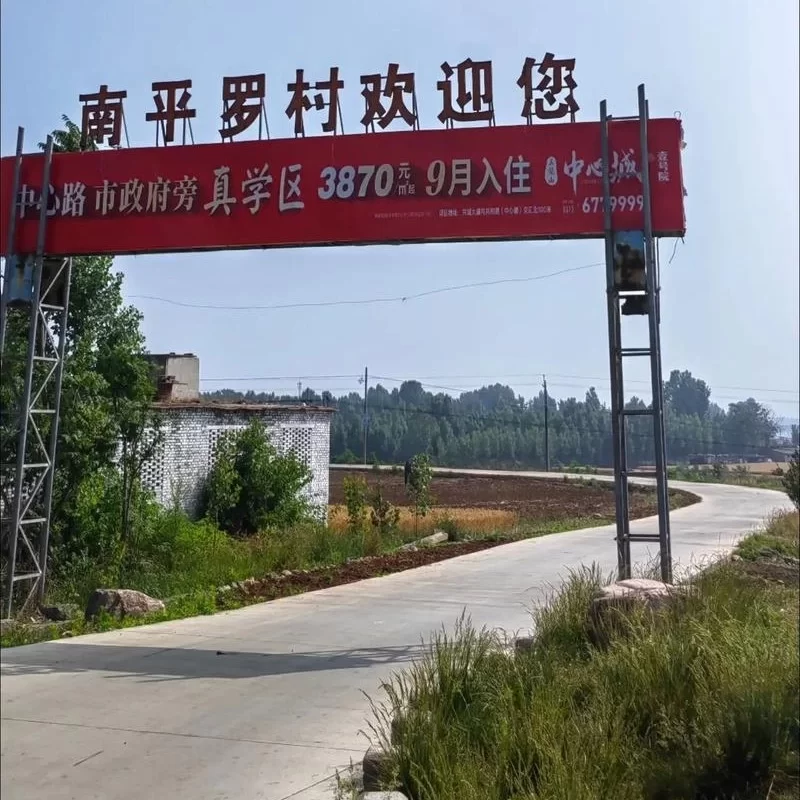
印象五、西平罗村:老槐树下的故事,比芜湖古巷更有温度
走进西平罗村时,最先撞见的是村口的老槐树——比芜湖巷子里的老皂角树更粗壮,树干得两个人合抱才能围住,树皮裂开深深的纹路,像老人的手掌,摸上去糙糙的,却透着股踏实的温度。树干上钉着块“拴马槐”的牌子,红漆有些剥落,“当年刘伯承的战马就拴在这儿,马蹄在石头上踏出的凹痕,到现在还在。”村里人指着树根下的一块青石板说。我蹲下身摸那凹痕,冰凉的石头上似乎还留着战马的体温,风一吹,槐树叶沙沙响,像在低声说过去的事。

祠堂里,92岁的李大爷正坐在门槛上晒太阳,右腿有些瘸,裤脚挽起来,能看见一道浅浅的疤痕,像条淡褐色的线。“当年抬伤员,被鬼子的炮弹片划的,流了好多血,以为活不成了。”他指着墙上的老照片,照片里的八路军战士背着枪,站在祠堂的院子里,笑容亮得像太阳,“陈赓的指挥部就设在村东头的磨坊,俺们半夜摸黑送军粮,十八盘的路,全是石头,鞋底磨穿了三双,脚底板全是泡。”

离开辉县那天,汽车站又遇见了背竹篓的老汉,竹篓里装满山核桃,硬壳上还沾着泥,他往我手里塞了两把:“带点回去,给娃们尝尝太行的味道,比你们芜湖的瓜子香。”汽车开动时,我透过车窗看太行山,轮廓渐渐模糊,可手里核桃的涩香、挂壁公路的凉、百泉湖的甜、万仙山的云海、西平罗村的故事,都留在了心里。

原来网上的评价从不是辉县的全部——它的好,不在刻意的宣传里,在每一次指尖触碰岩壁的糙、每一口呼吸里的松香、每一个老人眼里的光里。这趟太行行,不是看风景,是把一份沉甸甸的心动装回了家,往后再看芜湖的山水,心里总会多一份牵挂:那片红石绝壁上的阳光,那汪千年泉眼里的泡泡,都在等着再去看看。






评论(0)